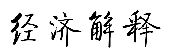13日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让人心痛。这场由“IS”组织并策划的系列枪击案,截至目前,已有129人死亡,300多人受伤。
在死亡的7名凶手中,由6名是引爆炸弹身亡的。也就是说,这次仍是自杀式袭击。而从籍贯上看,凶手有比利时籍,也有法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,且至少一人是通过“难民”途径进入,并在叙利亚受训过的“圣战分子”。
从机会成本看自杀式袭击
恐怖分子身绑炸弹袭击平民,说明行动前已知必死无疑。是什么原因造就了如此极端“损人害己”的“人弹”?从机会成本看,不惜一死的恐怖分子,说明在他的行为选项中,死亡的代价等于零或为负,生不如死。也就是说,当恐怖组织指派某人做人弹时,被指派者已知免不了一死。若不进行自杀式袭击,组织可能会让他或其家属死得更惨。若执行了组织指令,不仅可得到“烈士”的荣誉,通常家属也会得到一笔补偿金。横竖是死。而在炸死他人中丧命,对自己还是有利一点。自杀式袭击并没有推翻经济学“自私”的假设。
不排除由于愚蠢(经济学意义上的“讯息费用”高)而被极端教义派蛊惑,受成为“烈士”的引诱而做人弹的可能。但只要生有所得,生有所欢,面对死亡,被指派者总会进行反抗。生有所得,生有所欢的“收入”越大,激起的反抗一定会越激烈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除了被逼外,自愿加入极端教义派充当人弹的,一定是实际生活中的低收入者。是的,贫穷增大了做人弹的概率,富人谁会愿意做人弹?这也是机会成本所致了。
一个人,只要生稍有所得,生稍有所欢,总不至于去主动送死。实际上,从现有的案例看,绝大多数充当人弹者多是被组织逼迫的。也就是说,恐怖组织要制造一颗“人弹”其实并不容易,要用尽各种手段。而要寻找人弹目标,也会从低收入的穆斯林信徒中找。由此推测,人弹是有限的。恰如长沙理工大学朱锡庆教授所言,若人弹容易制作,以极端教义派的力量,这个世界早被炸个稀巴烂了。
这次巴黎恐怖袭击中有女性参加。而近年的人弹袭击中,也时常见到穆斯林女性。是因为在某些穆斯林教义的实际运作中,女性身体的产权是完全界定给丈夫、父亲或兄弟的,他们享有生杀予夺大权。一旦家族的男人成为组织者或策划者,这些妇女就很可能成为人弹。近年在德国,还时常爆发“荣誉谋杀”案。即在某些穆斯林家庭中,父亲或兄弟认为家庭某一女性的行为令家族“蒙羞”,而直接将其杀掉,完全无视世俗法律的禁止。这给反恐带来的重要提示是,在这一特殊局限下,某些穆斯林女性被迫做人弹的概率是较高的。
由于在武力上不能与欧美直接抗衡,近年来,恐怖组织主要采用的方式就是防不胜防的人弹袭击。反恐不外有两种方式。一是从肉体上消灭恐怖分子,减少存量。若恐怖分子脸上写有“恐怖”二字,打击易如反掌。正是由于难从众多的穆斯林人群中分辨出恐怖分子,所以彻底消灭不可能。除了尽可能的预防外,更好的做法是打击恐怖组织,尽可能挤压其生存能力和空间。二是控制流量,尽可能提高穆斯林族群的生活水平,降低他们成为恐怖分子的可能性。
遗憾的是,欧美在这两方面做得都不够好。中东和北非政策的失误为“IS”这类极端教义派提供了生存和成长空间。而欧债危机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普遍下滑的同时,高福利政策养懒人,也阻碍了欧盟内部穆斯林信徒生活的改善和文化的融入。近年的案例表明,越来越多的恐怖分子来自欧盟内部的穆斯林。“家贼”更难防了。
“IS”的崛起和中东政策的失误
这里无意回顾并梳理欧美百年来的中东和北非政策,仅以“IS””的崛起为例,来说明其政策的“蛮横”和“天真”是如何酿错的。
以“9.11”事件为由,美国以武力推翻了萨达姆的独裁政权,并幻想在伊拉克建立民主,为中东树一模板。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以“选票”上台,却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教派和解,换来的不过是反过来什叶派对逊尼派(包括库尔德人)的压制而已。沙达姆推行的政教分离政策反而被弱化了,而作为伊拉克国家统一基石的“国民卫队”,也被强制解散。被打压之下,位于伊拉克中西部的逊尼派反支持“IS”在此地存活,并在一定程度上掩护,助其成长。因为“IS”对抗政府军,要消灭的不是逊尼派,而是什叶派、基督徒、犹太人和异教徒等。
2011年“阿拉伯之春”后,欧美又与阿盟结合,借与伊拉克接壤的叙利亚内乱之机,想推翻巴沙尔政权,以使占人口多数的逊尼派掌权,拆散在这个地区存在几十年的什叶派联盟,切断伊朗对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支持,从而把波斯人的势力赶回波斯湾。
讽刺的是,“IS”的母体就是叙利亚境内反巴沙尔政权的基地组织,最初的成长就获得了美国、法国的支持。随着巴沙尔政权的被削弱,成长起来的“IS”立马调转枪口,对准欧美、沙特和以色列等。在打通了叙伊边界后宣布建国,阿盟和欧美不得不吞下这意外的苦果。中东的核心区域陷入了更深的动荡和失序中。巴沙尔政权被赶到地中海东岸,而伊拉克四分五裂,政治意义上的统一版图已不复存在。
苦果不单单是“IS”一例。因金融危机而爆发的“阿拉伯之春”,从表面上看,推翻了独裁的强人政治,穆巴拉克、卡扎菲、萨利赫、本.阿里等人下台。但结果不是预期想象的天真,是一场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,反而迅速演变成“阿拉伯之冬”。中东和北非陷入更深的动荡和失序中,包括“IS”等更多的基地组织反而得以发展壮大。
道理再简单不过。穆巴拉克等政治强人即使有种种不是,施行的不是明智独裁。但毕竟都是欧美之前的反恐盟友,他们推行的是政教分离,世俗化的政策,会尽其所能地打击主张政教合一,主张消灭世俗政权和异教徒的激进教义派。而一旦他们下台,该地区连秩序都无法提供,这正给基地组织的发展和扩散提供了可乘之机。突尼斯、利比亚、也门和埃及等基地组织余孽死灰复燃。上月底在埃及境内被袭击的俄罗斯客机,“IS”就声称是其西奈分支的“勇士”所为。尽管尚未被确认。
整个北非和中东地区,宗教林立,教派对立,政体不一,民族矛盾复杂,历史恩怨难解,产权界定不清。拉远镜头看,这个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和争斗,类似处于远古的部落战争时期,以实力为基础的较量不可避免。想通过政治谈判和外力强压,来达到政治平衡,几无可能。更何况欧美还夹杂着自身的利益诉求,裁决者的身份存疑,裁决时也难做到不偏不倚。幻想以投票来实现内部的良治,结果是连最基本的秩序都成了问题,反成了恐怖组织蔓延的温床。
高福利的无穷祸害
欧洲的高福利是二战后加速形成的,因为之前毕竟还有财政收支平衡的约束。但战后凯恩斯主义为政府的举债度日提供了理论论证,于是,政府开始包办民众的养老、医疗、教育等福利。甚至有些政府还为光棍发“嫖妓”津贴,以满足他们的性需求。
“免费”多,福利高看上去当然好,但最终“钱”来自于何处?只有来自财政收入,来自纳税人。全球高福利的国家,无一例外高税率,且富人的边际税率要远高于穷人。当税收不能填补高福利的支出时,就发债。当有一天连利息都付不起,再无人愿意借钱,老债不能展期,唯有宣布破产“重组”。这就是2010年爆发的“欧债危机”。
“高福利”的最大弊病是使整个国家的劳动力定价体系出错。在边际税率上“打富”和在各种补助上“济贫”,导致收入不再是自身努力和知识量的函数,努力工作者与“懒汉”的收入在边际上近乎相等时,谁还会选择努力工作?更致命的是,知识或人力资本的积累多是靠“干中学”,高福利毁掉了人力资本积累的通道,使得一个国家失去了长久的竞争力和赖以安身立命的根基。一些国家两百多年工业化累积的财富,被几十年不到的“坐吃山空”,吃破产了。
当前,欧洲正在经历去债务化的进程。劳动力的工资和民众的生活、福利水平必须大幅下调,才能在全球市场重新赢得竞争力,重返增长通道。显而易见,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。希腊的债务重组闹剧一出接一出,即是明证。
欧盟内现在有2000多万穆斯林,主要集中在英法德意几个大国,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二战后的移民。这些移入的穆斯林受自身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约束,收入也较低。从英法德的情况看,他们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贫民区中,靠领取福利金过日子的比例也较高。这在福利较高的法国表现的最为突出。
面对未来的去债务化,欧盟诸国不得不降低民众的福利水平。收入较低的穆斯林显然受到的影响较大,引发的怨怒会较多。从上面的分析可知,恰是之前的高福利,使得他们可以“不劳而获”,能养活自己和家人,结果反而阻碍了他们通过辛勤劳动,在“干中学”中累积知识,从而提高收入,向上流动。法国与美国恰可形成对比。由于美国的福利水平相对来说较低,移入美国的穆斯林必须要辛勤工作,才能养活自己和家人,结果反而能较好地融入美国社会。
高福利带来的另一个祸害是由于政府兜底进行社会养老,不用养儿防老后,欧盟生育率低于人口新陈代谢所需的水平,快速步入老龄化。这在福利很高的北欧和西欧呈现的最明显。发展需要新移民。同处地中海沿岸,地理位置较近的天然优势,使得移入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成首选。但在高福利的局限下,若移入的穆斯林只是领取社会福利过日子,等于是切分了移入国民众的“蛋糕”,使得他们能分的份额减少,自然会引发“抵制”。因此,每到欧盟内各国的大选年,移民政策都是政党激辩的焦点问题之一。
在当前工资和福利要大幅度下调的背景下,移入国必然对移入的穆斯林设置种种标准。网上流传的那段默克尔与巴勒斯坦难民女孩的对话,其明显的尴尬与“无情”,即缘于此。而对以“难民”或其他身份已经移入的穆斯林,在是否立即享有与原居民无差别的社会福利上,也会设置“年限”等标准。这无疑是做了“三六九等”的区分,含有“歧视”的意味。若新移入的穆斯林在市场竞争中落败,难免不把落败原因归咎于“歧视”,而心生怨恨。
也就是说,欧盟内部的高福利使得移民成为必然选择。但高福利又不利于人力资本含量较低的穆斯林通过辛勤劳动,提供收入来融入当地社会。而在“饼子”有限的情况下,又必然导致约束和“歧视”新移入的穆斯林。未来福利必降时,低收入的穆斯林群体受到的影响又首当其冲。在穆斯林问题上,高福利的危害,何其大也!
“歧视”的困境
最后谈一下恐怖袭击频繁带来的“歧视”困境。由于恐怖袭击是穆斯林造成的,且近年来更多的是内外结合的有组织谋划。这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欧盟内非穆斯林看穆斯林的眼光“异样”,在言辞或行动上的防范及“歧视”。欧盟内温和的穆斯林占绝大多数,他们也是恐怖袭击的“受害者”,尽管是“间接”的受害者。
要指出的是,这种“歧视”是恐怖袭击带来的一个“副产品”,无可避免。原因就在于上面所分析的,在众多的穆斯林中辨别出恐怖分子的知识缺乏,导致讯息费用太高。而恐怖袭击带来的伤害巨大,非穆斯林只能采用反推法,把所有的穆斯林都视为可能的恐怖分子,进行防范,从而必然产生言辞或行动上的“歧视”。
这种“歧视”会随着恐怖袭击的减少而自动消失,不必过于担心。反恐还是要从反思欧美的中东北非政策,进一步挤压极端教义派的生存空间入手。同时,设法增加穆斯林的收入,提高其生命的机会成本。